| 分享到: | 更多 |
这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
我谈文学史别有幽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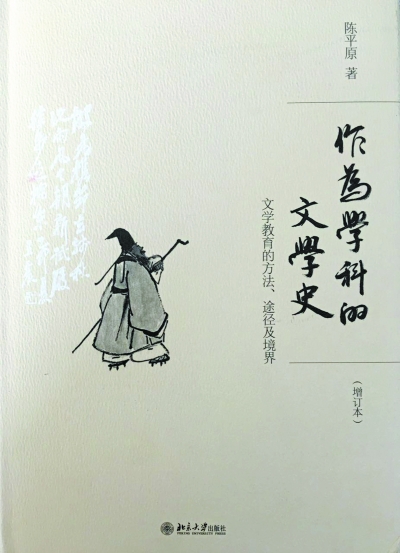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比起古老的“文赋”、“诗品”、“词话”、“曲录”来,“文学史”无疑是小弟弟。可这位后起之秀,一出生就身手非凡。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科目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国文学史”等,并提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从那时起,中国人便开始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心。得益于“科学”精神、“进化”观念以及“系统”方法的引进,“文学史”在现代中国学界所向披靡,百年后的今天,已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
多年前,我在讨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为什么?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如此立场,今天我仍坚持——“文学史”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文学教育的展开。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一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
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深入体会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学者立场与时代氛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众多努力中,我尤其注重从教育角度切入。论及前辈学者,世人多看重其传世之作,但据此判定教授的功业则不无偏颇。引入早就随风飘逝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教学”与“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是希望进一步落实大学教书育人的功能。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方能在“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
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因此,《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一书既总结百年来中国人从事文学史撰述与教学的经验,又质疑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辨析得失的同时,更希望探究可能的出路。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
记得我第一次认真讨论文学史问题,是二十年前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其中有这么一句:“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日后我的很多论述,都是围绕这句话打转。相对于学界其他同仁,我之谈论文学史,更多地从教育体制入手,这也算是别有幽怀。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谁动了科技考古毕业生就业的奶酪? | 2014-03-20 |
| 我们为何要打造“中国学”学科 | 2014-03-20 |
| 观点摘编:把文艺学和文学理论两种称谓统一... | 2014-03-20 |
| 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 | 2014-03-20 |
| 读经典,收获的不只是粮食,更是种子 | 2014-03-20 |
| 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是当务之急 | 2014-03-20 |
| 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文学 | 2014-03-20 |
| “文化自觉”是对西方人类学的一种回应 | 2014-03-20 |
| 改变我们的语文课程形态 | 2014-03-20 |
| 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 | 2014-03-20 |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95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