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危机和之前有何不同?或许可以乐观地说,当代地缘政治危机(如9·11和叙利亚内战)无论如何夺人眼球,在毁灭性上也不可能与上世纪动辄千万人殒命的世界大战相提并论。这正是平克(Steven Pinker)敢于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论证人类历史进步观的原因。然而,为什么我们对危机的感受却比父辈更强烈呢?克鲁克山克(Ruth Cruickshank)在《危机的美学》一书中认为,作为转折点的危机在当代变为了一种修辞,被媒体和市场不断地构建和操纵,目的是为了让全球市场经济永远存续下去。尽管当今全球危机的烈度在降低,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在加强,但危机作为一种话语却被前所未有地媒介化,成了后现代的典型景观。硅谷的产品发布会,好莱坞的科幻灾难大片,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视频……危机叙事无时无刻不在流通和复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算法甚至还能向用户推送符合阅读期待的危机新闻。随着我们在21世纪感知现实和交流沟通的方式变异,泛滥的多媒体影像正将危机嵌入大众的想象与无意识,左右了我们的叙事程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回到世界文学的话题。我的基本假设是:随着时代危机的变化,世界文学在新世纪也具有了新的面相,呈现了新的问题性。首先,学者们仍在激辩到底什么才是“世界文学”。如韦勒克(René Wellek)所言,可以广义地说世界文学是所有文学的集合,但这种定义相当于让研究对象变得漫无边际。即使如韦勒克、奥尔巴赫般博学的读者,也不可能穷尽各时代、各民族以不同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象,而是问题本身,它需要新的批评方法”,并由此呼吁从对文学正典的“近读”,转向对海量文本的“远读”。在莫雷蒂看来,克服学科危机的出路是数字人文(DH),即让计算机帮助我们处理文本,解析文学在全球旅行中的文类演化规律。当然,韦勒克指出还有一种狭义的世界文学,即挑选出各民族文学中的代表作,然后将它们遴选为世界文学的成员。但这种做法显然容易招来诟病,因为拣选即意味着权力,它往往与西方政治与经济霸权的运作密不可分。尽管《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已经厚达六千多页,力图网罗世界文学的经典,但主编工作仍由英美学者担任,出版由美国商业机构把持,而阅读对象也几乎都是北美大学生。
对于这种“美式风格的世界文学”,后殖民学者斯皮瓦克多有指摘,认为它背叛了民主的理想,使得世界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沦为文化霸权国家主导的强者游戏。而阿普特(Emily Apter)在《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中则警告我们,第三世界文学一旦被翻译成英语,它们内在的差异性就被取消了。加州大学教授马夫蒂(Aamir R.Mufti)在其新著《忘记英语!: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中表达了相似的不满。他的基本观点是,自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出现的世界文学,伴随着同时期西方知识界“东方学”的形成,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即使不是一码事,至少也密不可分。除了对世界文学的谱系学做了福柯式考古,马夫蒂还进一步指责当前世界文学成为了西方强国操控的人文研究领域,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推动,世界文学才会在21世纪伊始出现强劲的上升势头,渗透到全世界的教学、研究、出版和阅读等诸多领域。以最具影响力的哈佛大学世界文学暑期研习班为例,虽然自2011年创办至今,曾在北京、伊斯坦布尔、香港、东京等地轮流举办,但研讨班的核心依然是以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为代表的北美学术圈精英。显然,尽管莫雷蒂主张在世界文学的研究中剥离民族历史书写,马夫蒂却坚持认为它们在新世纪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世界文学的这种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否即意味着“文化帝国主义”呢?弗雷德里希 (Werner P.Friederich)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认为,世界文学这个提法口气何其大,简直是个“充满无知和傲慢的术语”。马夫蒂的敏锐之处,在于他发现了当前“世界文学热”背后的“单一世界思维”(one-world thinking),这种思维将世界想象为“一种连续的、可跨越的空间”。当年,歌德和马克思预言世界文学即将到来,判断依据是世界市场的形成;时至今日,这种全球市场早已成为现实,文学和各种商品一样卷入了全球化的高速流通(中国读者手握Kindle阅读器,一键购买亚马逊书店的最新小说,几秒钟之后就能开始阅读)。然而,马夫蒂警告我们不要被这种看似无边界的世界所迷惑,因为这种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并不对等。诚如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中所言,全球化一方面制造了那些坐在喷气飞机公务舱的 “游客”(tourist),同时也造就了那些被迫迁徙或毫无流动能力的“流浪者”(vagabond)。将世界文学想象为去边界化的自由国度,这或许有些天真。
在这个意义上,马夫蒂的书是对于卡萨诺瓦(Pascal Casanova)和达姆罗什的一种激烈挑战。对前者而言,世界文学空间内的边界、资本和流通应该与政治和经济的世界区分开来。卡萨诺瓦不认同全球资本主义对文学的主宰性,她划出了一个“文学场”,认为文学哪怕不是自在而为的独立精神世界,也绝不是政治经济的提线木偶。卡萨诺瓦依照一种“精神经济学”来考量文学产品的制造和流通——执牛耳者是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乔伊斯、福克纳和贝克特,他们所拥有的强势地位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无关,而是依据文学正典内部所形成的不朽审美标准。当少年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如痴如醉地听着父亲讲述遥远的前宗主国的文学名著时,他与毛姆、狄更斯、奥威尔笔下那些迷人小说之间的引力,也绝非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一说可以解释。简言之,马夫蒂希望对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建制做历史化和政治化的分析,而卡萨诺瓦则是从欧洲文学的接受史、影响史中寻找世界文学的自主性(autonomy)和特异性(singularity),呼吁对世界文学去政治化、去历史化。
而对达姆罗什而言,世界文学与其说是一个研究领域,还不如说是一种“阅读模式”。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取决于文学的世界旅行,即离开文本产生的民族疆域并进入到世界语境中,让作品在跨文化翻译和接受中获得全新的生命。对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世界文学意味着获得一种新的认识论,因为它往往需要读者跳出固有的审美和认知模式,与他者的文学形式或属民视角进行积极的接触。达姆罗什承认,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进入西方,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东方主义偏见挟裹,或被霸权文化他者化,但这绝不是全部的真相。马夫蒂或许过分强调了东方主义思维或后殖民政治的权力逻辑,以至于不相信西方学术界内部有可能不屈从于世界文学的制度化,进而反思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反讽的是,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马夫蒂都是北美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他们本人就是这种西方人文学科制度化的产物。对于北美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学科建制的尖锐批评,恰恰诞生于这种制度的内部。
最后我想思考的是,当21世纪的世界文学面对内忧外患,是否还有“第三种道路”的可能?或者说,在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文学空间”和泛政治化的殖民话语批判之间有无更好的选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首先要重新定义 “世界”和“文学”。世界文学不应被仅仅视为一种历史建构物或摹仿的方法,而是具有自身能动性的力量,能对之前论及的全球危机施加影响,也能参与到当代世界的构建和转变中。这里,普希纳的观点或许颇值得借鉴。他认为“世界文学就是那种关乎世界的文学”,并将之命名为 “世间的文学”(worldly literature)。他反对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来界定世界文学是什么,而是主张考察世界文学能做什么——既不将之放入纯粹的精神国度,也不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盘中餐。或用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话说,世界文学“诞生于文学和政治遭遇的淌血的黑暗十字路口”,它一方面无法摆脱政治的压迫性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自己的反作用力。
这种将世界文学视为事件性存在的观点,在谢平(Pheng Cheah)广受好评的新著《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中获得了某种理论共鸣。这位加州大学的华裔学者从海德格尔的“世界”(Welt)概念出发,像斯皮瓦克那样将“worlding”视为一种“世界建构”的过程,而世界文学则成为了这个过程中与全球资本流动进行对抗的“规范性世界力量”(a normative worldly force),其意义在于破坏和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设定的世界图景和目的论时间。当然,谢平并未一厢情愿地认定文学可以力挽狂澜,他承认世界文学的力量其实相当脆弱,因为世界市场处于力量的巅峰,西方现代性正在主宰和规划“进步”的路线图,并激烈地摧毁其他类型的世界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时间性(temporality)。但即便如此,世界文学依然不应气馁,毕竟它所讲述的仍然是“表达世界开放性的最佳叙事方式”。如果放任世界文学萎靡和消亡,我们今后面对的将只有那些被商业化大众传媒营销的危机叙事。
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曾说,在这个后9·11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还需要艺术化的再现方式,是因为它能帮助当代社会纾解极端恐怖事件带给人类的宿命感或无力感。当世界文学在危机重重的时代坚持发声时,文学家就重新夺回了叙事的控制权,进而改变了情节的发展方向。我愿意相信,世界文学比商业社会的类型化叙事更有力量,凭借文学独特的想象力和审美距离,我们可以更有力地去质询那些建构世界的主导性力量,更有尊严地在21世纪全球危机中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
(作者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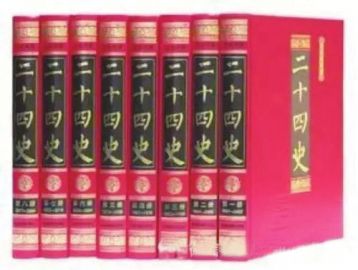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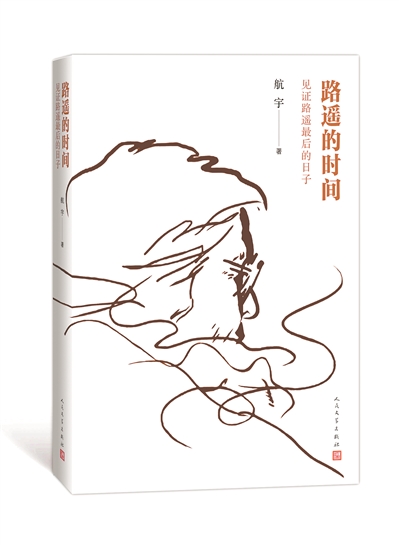











 ×
×